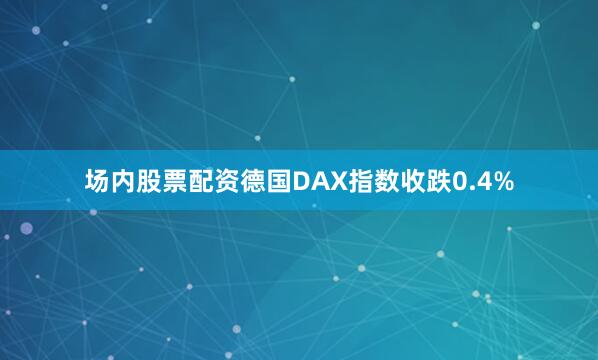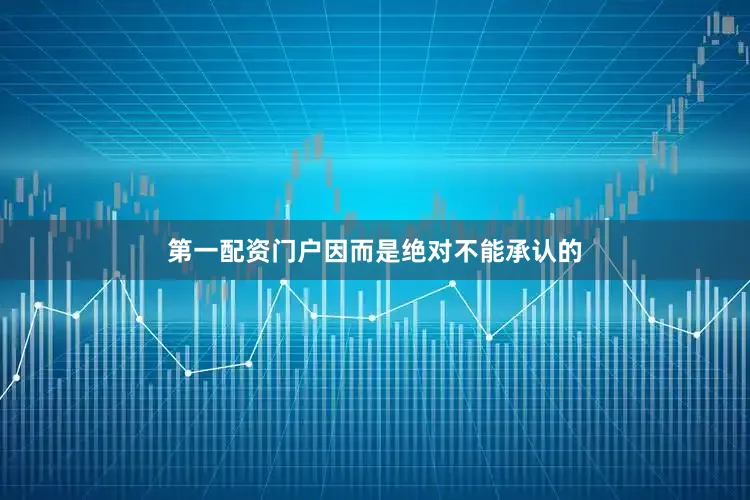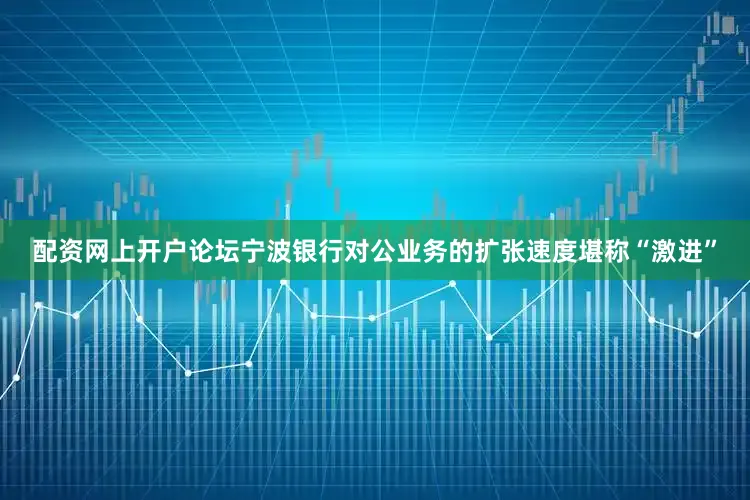
出品:山西晚报·刻度财经
一连串两位数的增长数据,延续了这家城商行的“优等生”光环。
8月28日晚间,宁波银行正式对外披露2025年半年报。上半年,宁波银行营业收入371.60亿元,同比增长7.91%。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7.72亿元,同比增长8.23%。与中报一同公布的,还有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预案,拟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3元(含税)。
资产总额突破3.47万亿元,较年初增长11.04%;贷款及垫款余额1.67万亿元,较年初增长13.36%;客户存款余额2.08万亿元,较年初增长13.07%。一连串两位数的增长数据,看似延续了这家城商行的“优等生”光环。
展开剩余93%但回溯陆华裕执掌宁波银行的近20年,从2005年接棒行长、2014任董事长至今,“规模扩张”始终是贯穿发展的主线。
如今,当银行业步入息差收窄、风险暴露、转型承压的“新常态”,宁波银行半年报显示,息差持续收窄只能靠规模填补,不良率“维稳”依赖规模稀释,盈利增长绑定规模扩张,曾经凭借差异化优势突围的宁波银行,正深陷“规模依赖症”的泥沼,而掌舵20年的陆华裕,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破局考验。
01
息差“跌穿地板”
财报显示报告期内,公司年化净息差1.76%,较2024年同期下降11个基点;年化净利差1.79%,较2024年同期下降14个基点。这已经是宁波银行息差连续多个季度收窄,从2023年上半年的1.88%到2024年上半年的1.86%,再到2025年上半年的1.76%,净息差如同“温水煮青蛙”般持续承压,资产端定价能力的全面失守。
2025年上半年,公司生息资产平均余额2.93万亿元,同比增长18.40%,但生息资产平均收益率却从2024年上半年的4.05%骤降至3.58%,降幅高达47个基点。
其中,作为资产端核心收益来源的贷款业务,表现更为惨淡,贷款平均收息率从2024年上半年的4.92%跌至4.38%,下降54个基点,直接反映出在LPR下调、存量房贷利率调整、市场竞争加剧的多重冲击下,宁波银行对贷款定价的“话语权”正快速流失,正陷入“收益降、规模补”的恶性循环。
为了维持贷款规模增长,宁波银行不得不加大低收益资产的投放力度。报告期内,票据贴现余额1396.99亿元,较年初增长45.98%,占贷款总额的比重从2024年末的6.48%提升至8.35%。在银行业务中,票据贴现本就是“冲规模、占额度”的典型低效益业务,其收益率通常远低于对公贷款和零售贷款。
如此激进地扩张票据业务,本质上是对公有效信贷需求不足的“无奈之举”,当优质企业信贷需求有限时,只能通过票据业务填充规模,以“量”的增长掩盖“价”的颓势。
2025年6月末,公司贷款余额9982.04亿元,较年初增长21.34%,占贷款总额的59.66%;而零售贷款余额5353.10亿元,较年初下降4.02%,占贷款总额的31.99%。公司贷款的高速增长,看似是对公业务的“强势突围”,但结合票据贴现的激增不难发现,其中大量贷款可能并非投向高收益的实体企业项目,而是以低收益的票据形式存在。
2025年上半年,公司客户存款平均付息率1.71%,较2024年同期下降25个基点,这主要得益于活期存款占比提升与存款利率市场化下调。但从负债结构来看,宁波银行对短期主动负债的依赖正不断加深,2025年6月末,拆入资金余额2113.63亿元,较年初增长10.12%;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余额2763.10亿元,较年初增长69.24%。
2025年上半年,公司利息净收入257.26亿元,同比增长11.11%,看似保持了两位数增长,但这一增长完全依赖生息资产规模的扩张,若剔除规模增长的影响,仅考虑息差收窄的因素,利息净收入的实际增速可能已接近个位数。这种“以量补价”的盈利模式,不仅可持续性存疑,更会随着规模的进一步扩张,加剧风险积聚。宁波银行正陷入“规模越大-息差越窄-规模更要大”的恶性循环。
02
不良率“维稳”假象
在规模扩张的掩护下,宁波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依旧维持在0.76%的“低位”,这一数据不仅低于行业平均水平(2025年上半年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约1.10%),也与自身年初数据持平,看似资产质量“稳如泰山”。但穿透数据表象,这份“稳健”实则是规模稀释下的“假象”,不良贷款余额的增长、结构风险的暴露以及拨备覆盖率的下降,都预示着资产质量的隐忧正在加剧。
截至2025年6月末,宁波银行不良贷款余额126.88亿元,较年初增加14.21亿元,增长幅度与贷款规模13.36%的增速基本持平。宁波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之所以能够维持稳定,并非因为资产质量的实质性改善,而是依靠贷款规模的快速扩张进行“稀释”。
打个简单的比方:若贷款规模增长13.36%,不良贷款余额同步增长13.36%,不良率自然保持不变,但这并不代表新增贷款的资产质量没有问题。
2025年上半年,个人贷款余额较年初下降4.02%,但不良贷款余额却未见明显下降,其中个体经营贷款不良率高达3.30%,是整体不良率的4倍多;个人消费贷款不良率1.83%,也远超整体水平。个体经营贷款主要投向小微企业主、个体工商户,受经济周期、消费需求影响极大,3.30%的不良率反映出小微企业的经营压力正通过信贷渠道传导至银行;而个人消费贷款不良率的高企,则说明居民端信用风险也在上升,这与上半年消费需求疲弱的宏观背景高度契合。
宁波银行关注类贷款迁徙率34.99%,虽然较2024年的52.60%有所下降,但34.99%的水平仍处于高位。关注类贷款迁徙率是衡量资产质量潜在风险的重要指标,34.99%意味着每100元关注类贷款中,有34.99元可能转化为不良贷款。
截至2025年6月末,宁波银行关注类贷款余额171.02亿元,较年初增加18.99亿元,若按照34.99%的迁徙率计算,未来将新增约60亿元不良贷款,这无疑会对不良率形成巨大压力。
2025年6月末,公司拨备覆盖率374.16%,较2024年末的389.35%下降15.19个百分点,较2023年末的461.04%更是下降86.88个百分点。拨备覆盖率是银行抵御不良风险的“缓冲垫”,374.16%的拨备覆盖率虽然仍高于监管要求(≥150%),但持续下降的趋势却不容忽视——这意味着宁波银行抵御不良风险的能力正在逐步减弱,若未来不良贷款加速暴露,拨备覆盖率可能进一步跌破350%、300%,甚至逼近监管红线。
2025年上半年,公司共计提信用及资产减值损失93.52亿元,同比增加21.90亿元,增长30.58%,其中贷款减值损失85.88亿元,同比增加18.83亿元,增长28.08%。计提规模的大幅增长,看似是风险防控意识增强,但结合不良贷款核销数据来看,却另有隐情,2025年上半年,公司核销不良贷款59.71亿元,较2024年上半年的139.69亿元大幅下降。
一边是计提规模的增加,一边是核销规模的减少,本质上是通过“多提少核”的方式人为维持不良率稳定,这种做法虽然短期内能让财报数据“好看”,但长期来看,会导致不良贷款“堰塞湖”的形成,一旦经济下行压力加大,不良率可能出现“断崖式”上升,存在“以提代冲”的嫌疑。
此外,贷款拨备率(贷款损失准备占贷款余额的比例)也从2024年末的2.97%降至2025年6月末的2.84%,下降0.13个百分点。贷款拨备率是衡量银行整体风险抵补能力的综合指标,其下降进一步说明宁波银行在贷款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,风险抵补的力度并未同步跟进,资产质量的“安全垫”正在变薄。
03
对公“一骑绝尘”,零售“躺平”
陆华裕提出“大银行做不好,小银行做不了”的经营策略,依托对公与零售“双轮驱动”实现差异化突围。但从2025年半年报来看,宁波银行的业务结构正严重失衡:对公业务“一骑绝尘”,零售业务“躺平”收缩,子公司协同效应不足,曾经的“双轮驱动”沦为“单轮独转”,业务结构的抗风险能力大幅削弱。
2025年上半年,宁波银行对公业务的扩张速度堪称“激进”。截至6月末,公司贷款余额9982.04亿元,较年初增长21.34%,占贷款总额的59.66%,较年初提升3.93个百分点;对公存款余额15483.30亿元,较年初增长15.44%,占客户存款总额的74.57%。从数据来看,对公业务似乎成为宁波银行的“压舱石”,但深入分析便会发现,对公业务的增长更多是“量”的扩张,而非“质”的提升。
据悉,宁波银行对公业务中票据贴现余额暴增45.98%,占贷款总额的比重提升至8.35%。票据贴现业务的特点是期限短、收益低、风险相对较低,大量投放票据贴现,虽然能快速做大对公贷款规模,但对营收和利润的贡献却极为有限。
此外,从行业分布来看,宁波银行对公贷款主要集中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(18.27%)、制造业(11.61%)、批发零售业(9.63%),这三大行业合计占比39.51%。其中,制造业和批发零售业受经济周期、消费需求影响较大,2025年上半年,国内制造业PMI波动较大,批发零售业受消费复苏不及预期影响,经营压力较大,这些行业的贷款潜在风险不容忽视。
截至2025年6月末,公司贷款主要投放于浙江省(64.43%)和江苏省(22.55%),长三角地区合计占比86.98%,其中宁波市占比31.83%。区域集中度高,虽然能依托长三角地区的经济优势实现业务深耕,但也意味着一旦长三角地区经济出现波动(如外贸下滑、房地产调整、地方债务风险暴露),宁波银行的对公业务将首当其冲,资产质量和盈利水平都会受到严重冲击。
与对公业务的“激进扩张”形成鲜明对比的是,宁波银行的零售业务正陷入“躺平”状态。2025年6月末,零售贷款余额5353.10亿元,较年初下降4.02%,占贷款总额的比重从37.79%降至31.99%;零售存款余额5280.84亿元,较年初增长6.66%,增速低于对公存款(15.44%)和整体存款(13.07%)。零售业务的收缩,不仅背离了宁波银行“零售转型”的战略方向,也反映出其在零售业务拓展上的乏力。
零售贷款结构上个人消费贷款、个体经营贷款、个人住房贷款“三驾马车”均表现不佳。2025年6月末,个人消费贷款余额3452.43亿元,较年初下降3.43%;个体经营贷款余额889.12亿元,较年初下降12.69%;个人住房贷款余额1011.55亿元,较年初增长2.80%。
个人消费贷款和个体经营贷款的收缩,反映出宁波银行在零售信贷产品创新、客户拓展、风控模型优化等方面存在不足;而个人住房贷款的低速增长,则与房地产市场调整、居民购房意愿下降有关,但也暴露出宁波银行在房贷业务上的竞争力不足,2025年上半年,全国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同比增长约5%,宁波银行2.80%的增速明显低于行业平均。
2025年上半年,宁波银行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28.05亿元,同比增长4.04%,远低于营收增速(7.91%)。其中,银行卡业务收入6.8亿元,同比下降20.93%;代理类业务收入29.87亿元,同比增长10.06%;托管类业务收入2.06亿元,同比增长12.57%。
银行卡业务收入的大幅下降,反映出宁波银行信用卡业务拓展受阻,客户活跃度、消费金额可能出现下滑;而代理类业务收入的增长,主要依赖财富产品代销,这种“通道式”的中间业务,缺乏核心竞争力,受市场行情影响较大,抗风险能力弱。
为了打破单一银行牌照的限制,宁波银行先后设立了永赢基金、永赢金租、宁银理财、宁银消金四家子公司,试图构建“银行+基金+租赁+理财+消金”的综合化经营版图。但从2025年半年报来看,这些子公司的协同效应极为有限,更多是“各自为战”,未能形成“1+1>2”的合力。
从盈利贡献来看,子公司的表现“冷热不均”。2025年上半年,永赢金租实现净利润15.06亿元,是四家子公司中盈利最高的;宁银理财实现净利润4.21亿元;永赢基金实现净利润1.82亿元;宁银消金实现净利润2.50亿元。
四家子公司合计净利润23.59亿元,占宁波银行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(147.72亿元)的比重仅为15.97%,对集团盈利的贡献极为有限。
子公司与母公司的业务协同严重不足,以永赢基金为例,2025年6月末,其公募规模5447亿元,其中非货规模3586亿元,但这些规模更多是通过市场化渠道募集,而非依托宁波银行的零售客群;宁银理财管理的产品规模6011亿元,虽然与母公司有一定的代销合作,但未能与母公司的财富管理业务深度融合,未能形成“客户共享、产品互补、服务协同”的生态;宁银消金作为专注消费金融的子公司,其贷款余额、客户定位等关键信息未在半年报中详细披露,与母公司零售贷款业务的协同也无从谈起。
永赢金租主要从事融资租赁业务,其租赁资产的行业分布、客户资质、不良率等信息未在半年报中披露,若租赁资产集中于房地产、重资产行业,可能会面临较大的信用风险。
宁银消金在消费金融行业竞争加剧的背景下,其不良率、拨备覆盖率等风险指标也未披露,投资者无法评估其资产质量状况。这种“信息不透明+协同不足”的综合化经营,不仅无法提升集团的抗风险能力,反而可能成为集团的“风险隐患点”。
04
资本消耗加快,分红“短视”
随着规模的快速扩张,宁波银行的资本消耗速度也在加快,核心资本充足率持续下降;而在资本承压的背景下,公司仍坚持分红,反映出“短期利益优先”的倾向;此外,半年报中关键信息的模糊披露,也降低了公司治理的透明度,这些问题都对宁波银行的长期稳健发展构成挑战。
2025年6月末,宁波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9.65%,较2024年末的9.84%下降0.19个百分点;一级资本充足率10.75%,较2024年末的11.03%下降0.28个百分点;资本充足率15.21%,较2024年末的15.32%下降0.11个百分点。尽管三项资本充足率指标均满足监管要求,但持续下降的趋势却反映出公司资本消耗速度快于资本补充速度。
2025年上半年,公司发行89亿元二级资本债,用于补充二级资本,这也是公司维持资本充足率的重要手段。但二级资本属于“附属资本”,其占比过高会导致资本结构失衡,降低核心资本的抗风险能力。
2025年6月末,宁波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净额2172.96亿元,一级资本净额2421.39亿元,二级资本净额1005.12亿元,二级资本占总资本的比重达29.33%,这一比重虽然未超过监管限制(二级资本占总资本的比重不得超过50%),但也反映出公司对外部资本补充的依赖程度较高。
2025年上半年,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7.72亿元,扣除分红后,用于补充核心资本的金额约为127.91亿元(分红金额19.81亿元)。但同期风险加权资产净额从2024年末的20890.99亿元增至22525.88亿元,增加1634.89亿元,资本消耗速度远超内生积累速度。这种“外部融资依赖型”的资本补充模式,不仅会增加公司的融资成本,还会稀释股东权益,长期可持续性存疑。
在资本消耗加快、核心资本承压的背景下,宁波银行仍推出了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3元(含税)”的中期利润分配预案,分红金额合计19.81亿元,分红率(分红金额/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)达13.41%。从短期来看,分红能提升股东回报,提振市场信心;但从长期来看,这种“短视”的分红政策却牺牲了公司的长期稳健性。
一方面,分红会减少核心资本补充。19.81亿元的分红金额,若留存下来补充核心资本,可使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提升约0.08个百分点,缓解核心资本的承压局面;另一方面,分红也会削弱公司的风险抵御能力。在银行业息差收窄、不良风险上升的背景下,充足的核心资本是抵御风险的“第一道防线”,而分红则会直接减少这道防线的厚度。
对比同行业其他银行,宁波银行的分红政策也显得较为激进。2025年上半年,多家城商行(如南京银行、江苏银行)为了补充资本,纷纷下调分红率或暂停中期分红,而宁波银行却在资本承压的情况下坚持分红,反映出公司“短期利益优先”的倾向,未能充分平衡股东回报与长期稳健发展的关系。
从2005年到2025年,陆华裕执掌宁波银行的20年,是宁波银行从区域小行成长为资产超3万亿城商行的20年,也是“规模驱动”战略主导的20年。如今,当“规模依赖症”的弊端日益凸显,陆华裕若想带领宁波银行实现“二次突围”,就必须推动“自我革命”,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,从业务失衡转向结构优化,从外部融资转向内生积累。
宁波银行首先要做的,是彻底摒弃“规模崇拜”的惯性思维,将经营重心从“做大规模”转向“提升质量”。具体而言,一是控制贷款规模增速,将贷款增速从13.36%逐步降至10%以下,避免规模“虚胖”;二是优化贷款结构,减少票据贴现等低收益资产的投放,加大对科技金融、绿色金融、普惠金融等高质量领域的信贷支持,提升资产端收益率;三是强化定价管理,建立差异化的贷款定价机制,根据客户信用状况、行业风险、贷款期限等因素,灵活调整贷款利率,提升定价能力。
2025年,是陆华裕执掌宁波银行的第20个年头,也是宁波银行面临“生死抉择”的关键一年。20年的“规模驱动”,让宁波银行实现了从区域小行到城商行巨头的跨越,但也让其深陷“规模依赖症”的泥沼,息差收窄、不良隐忧、结构失衡、资本承压,每一个问题都在考验着这位掌舵者的智慧。
20年节点,陆华裕的选择,将决定宁波银行未来20年的命运。
发布于:北京市高忆配资-配资平台开户-炒股配资最新-炒股资金杠杆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- 上一篇:网上配资APP进一步拓宽公众对认知症的理解
- 下一篇:没有了